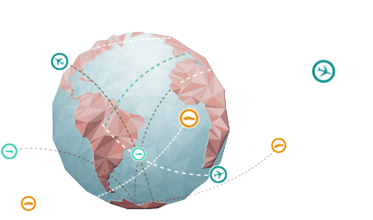國際條約和政府文件,看似冷冰冰,其實每一個字都充滿火藥味,這類文件的合約翻譯不是單純處理法律條文,還涉及文化認知、外交敏感度、語境政治性,甚至可能牽一髮動全局行情,對譯者來說,不只是「翻對」,還得「翻得起分量」。
國與國之間的文件來往,字眼的選擇具有策略意涵,像是英文中的 “shall” 與 “may”,中文若都翻成「應該」或「可以」,恐怕就落入模糊地帶,對國際談判桌上的律師來說,一個助動詞可能就代表責任義務與否,這不是語文小差錯,而是實打實的法律與外交立場,譯者若不熟悉公法、國際法甚至某些條約背後的談判歷史,很容易讓翻譯變成立場錯位的引信。
合約翻譯的行情,自然也不是按字計價這麼單純,碰上雙語版本具同等法律效力的合約(如中英對照或日英並行版本),每一條文字都必須經得起比對、挑戰與反覆協商,這種案子往往要與律師同步作業,有時甚至得接受外交部門或律師事務所的語義審查,這種級別的案子翻得越多,譯者的身價自然也往上爬。
還有一種情況更複雜,就是「譯文先行、原文未定」的草約草案階段,有些國際會議中,各方都以各自語言編寫協議條款,等翻譯完才逐字比對,看哪個語言版本能被接受,譯者此時扮演的不是「再現語言者」,而是「共同起草人」,這種情況下,不僅要求精通雙語,更要懂得法律文字的彈性寫法,懂得各方的談判風格、敏感詞和政治分寸。
譯者本身如果來自法律翻譯專業,通常也得跟得上各國對於文字表述的敏感程度,例如「同意」與「理解」在中英文中的法律效力差異、「承諾」與「聲明」的約束性強弱,甚至連一個逗點或換行都可能成為後續法律訴訟的爭點,沒有一點語言與邏輯神經,還真難長期駐守這個領域。
 政府文件的翻譯也不遑多讓,尤其是政策發布、白皮書、官方通告,涉及國際協力或對外表述時,更需小心翼翼,這種文體講求「話中有話」,有時字面柔和,實則強硬;有時語氣嚴肅,實為迂迴表態,翻譯時如果照字面直譯,容易讓立場變得僵硬;太過潤色,又可能被指失真,翻譯者得具備政治語言的解讀能力,還要拿捏住「不多說、不少說、剛剛好」的平衡感。
政府文件的翻譯也不遑多讓,尤其是政策發布、白皮書、官方通告,涉及國際協力或對外表述時,更需小心翼翼,這種文體講求「話中有話」,有時字面柔和,實則強硬;有時語氣嚴肅,實為迂迴表態,翻譯時如果照字面直譯,容易讓立場變得僵硬;太過潤色,又可能被指失真,翻譯者得具備政治語言的解讀能力,還要拿捏住「不多說、不少說、剛剛好」的平衡感。
報價方面,這類翻譯常採「專案制」,按頁數或文件級別計價,但真正的「行情」通常隱藏在專業信任感後面,律師、外交官、政策制定者信任你的語言處理能力,才敢把這種不能出錯的東西交給你,不是每個翻譯人都想做這一塊,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,因為它需要的不只是語言,而是長期的知識累積與法律敏感度。
國際合約和政府文件的翻譯,是一場語言與邏輯的高風險遊戲,沒人希望一紙翻譯造成國際爭端,但正因為風險高、影響大,也造就了合約翻譯領域譯者的高度專業價值,會翻字的人很多,能翻出分寸與立場的人,才真正站在語言與權力的交界線上行情。